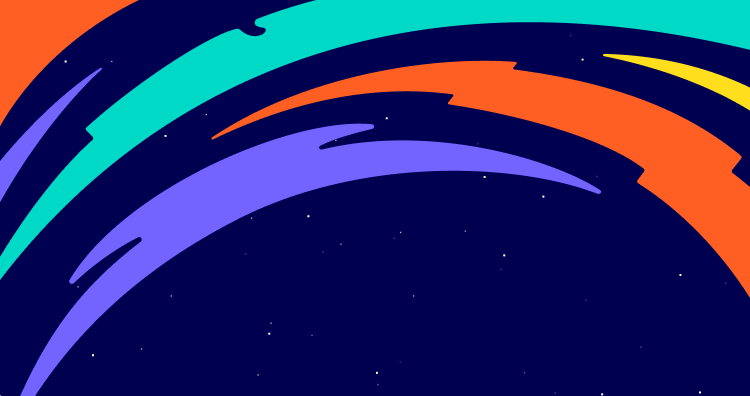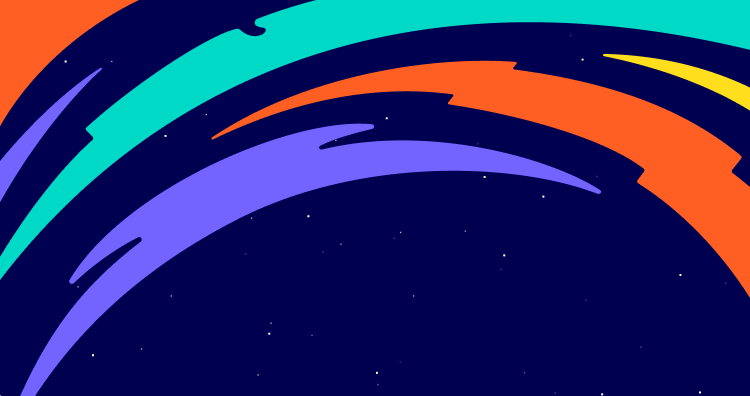《古代人生记》
【基于游戏内容改编,后续纯属脑洞造物】
我叫许栕,生于安朝载元三十四年。据我阿娘所言,我降生时,我的父亲,许逸,乐的合不拢嘴。取名为栕,是希望我效忠于帝,做为百姓遮风挡雨的“屋檐”。
父亲一生科举,四十岁那年参加殿试,可惜是“天子殿前走一遭,奈何榜上未有名。盼君来年八月八,满城尽带黄金甲。”
殿试落选,父亲只被草草地封了八品县丞,随意打发掉了。
父亲骄傲一生,童试乡试府试均为头筹,如何受得了这般委屈?在我一岁那年,也就是父亲受封八品那年,他辞了官职,毅然投湖。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立的遗嘱,竟将所有的遗产全部留给我——一个刚满一岁的襁褓婴儿。
阿娘冷氏是妾,她从未想过与主母争宠,自然也不在意我父亲的家产最后会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谁身上。也许正因如此,主母与我阿娘的关系甚为不错,亲如姊妹。可我继承了许家所有财产,主母气恨至极,与我阿娘断了交,主持完父亲的葬礼,便留下子女离开许家,再无联系。
父亲的长子,我的兄长许权,是父亲的另一房小妾岑氏所出。他还有两个同胞妹妹,但父亲似乎不大待见岑氏,连带着她的子女也一并不喜。
在我出生那年,父亲便将她逐出了家门。祖母本意是将兄长留下,他虽不得父亲宠爱,可毕竟是我许家香火。至于那两个妹妹,倒不甚在意。但那房小妾竟是偷摸着将兄长带走了,不知沦落到了何处,如今如何。
于是,香火旺盛的许家,一夜之间,只剩下我阿娘这一房的人,和父亲的一对嫡子女。
两岁时,父亲的遗腹子,我的同胞弟弟出生了。阿娘抱着他看着父亲的遗像,知道父亲最大的愿望便是入朝为官,效忠帝王,福泽百姓。可阿娘未曾入过几年学,不知如何取名能有寓意。于是照着我的名字为其取名,许桾。
五岁那年,疼爱我的祖母过世了,享年八十五岁。祖母眼中没有嫡庶之分,但她极为注重香火传承,偏爱于我与弟弟们。特别是我这个一岁就莫名其妙被父亲交付遗产的庶子,祖母更为偏爱。她坚信父亲的决定必然有道理,只是她一个妇道人家,愚笨,领悟不到。但在祖母固执的香火观念中也有意外的特例,那便是嫡姐,许悦。
嫡姐是家中的嫡长女,长我两岁,面容姣好,琴棋书画又样样精通,甚至诗词歌赋也略有涉猎,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男子,甚至更胜一筹。祖母曾无数次抚着嫡姐的头叹气,埋怨嫡姐为何不是个男子。那样,许家或许可以一门多状元。
嫡姐对此总是付之一笑,毫不在意。
七岁时,皇帝下旨在吴州府修建皇家行宫。占去了我家373亩田地,为此支付了14两黄金。而据阿娘所言,这只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之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继承的家产之庞大,我似乎理解了主母的不甘。父亲的嫡子许梧,在她看来才应该是这庞大家产的最合理继承人……
第一次独自上街闲逛时,时年九岁——也许不算,毕竟还有跟随的侍从。巧遇了民间杂耍,其中有一个女子生的灵动活泼,可惜杂耍技术欠了火候,但上蹿下跳的功夫倒是不错。杂耍结束,她拿着锣向众人讨要赏钱。
我欣赏她的灵动活泼,可惜她身为杂耍,阿娘不会允许我将她带回,怕误我学业。我随手丢了十文钱,那姑娘对我千恩万谢,不断重复着一句“谢过小少爷”。我看着她卑微地向众人讨赏,感谢,讨好,叹息着离开。
多亏父辈出息,才使得我不至于沦至她这般。
十一岁。
在阿娘的操持下,家里家外井然有序,我们兄弟姊妹之间也少有争斗,外人皆感慨阿娘的能干,赞颂阿娘教养有方,实为妻女楷模。
今年冬,恰逢大雪。雪初停,同胞妹妹许怜邀我一同去采雪煎茶吃。我在家中憋了几日,自是兴高采烈地陪她一同去。在我采雪之时,小妹调皮地抖落梅花枝上的雪,我霎时满身雪花,小妹在一旁笑的花枝乱颤。我无奈又好笑,采好雪后,随手弹了一下小妹的额头,她捂额,委屈巴巴的控诉我欺负她。
我轻斥一句:“也不知是谁先弄了阿兄一身雪的。”
她吐吐舌头,蹦蹦跳跳地和我回了家。
十二岁。
这年,十四岁的嫡姐许悦考中尚药局,孤身一人去了直隶省尚药局别院求学。
嫡姐临出远门时,阿娘为她收拾好了一切可能用上的东西,牵着她的手絮絮叨叨,望着嫡姐远去的背影满眼担忧与不舍。
阿娘养育嫡姐十一年,尽管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却早已亲如母女。我敬佩嫡姐,一介女流竟有勇气离开家乡独自求学。也再次感慨嫡姐生不逢时,为何不是个男子。
在嫡姐离家后不久,弟弟许桾便与巷子孩童起了冲突,互相投石相击。不巧被我发现,呵斥走了对方,心疼地发现他的额头被砸破了。
弟弟对额上的伤满不在乎,却央求我不要告诉阿娘。我犹豫,可到家还是告诉了阿娘弟弟今日发生的事。阿娘呵斥了弟弟的鲁莽,弟弟很伤心地解释那帮孩童说是阿娘赶嫡姐一人去求学的。阿娘沉默着替弟弟包扎好伤口,弟弟见阿娘伤心,不住地埋怨我多嘴。
我哑然,我怎知那帮孩童竟会说出这番言语呢?
十三岁。
妹妹许怜今年十二了,同母亲学了女红,她兴高采烈地将她绣的第一个香囊赠予我。我瞅着针脚粗鄙,形状不堪入目的香囊沉默许久,念在这也是妹妹对我的一片心意,我笑着收下,并夸赞了她几句。她一高兴,绣的所有香囊便全赠予了我……
这年的新年,阿娘为所有子女缝制了新衣,连远在直隶的嫡姐也没有落下。可弟弟妹妹包括嫡姐的新衣都到手了,我的新衣却不见踪迹。
我闷闷不乐,以为阿娘将我那份忘却了。
正月初一,我按例向阿娘请安。阿娘眉开眼笑,拉着我的手絮叨许多,我笑着应下。长兄被他生母带走后,我便是家中长子。所谓长兄如父,我既要顾学业,也要督促弟弟们学习,妹妹们学艺。因此每逢佳节的请安便成了我与阿娘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阿娘许久见不到我,独处时总要絮叨叮嘱许多。
絮叨到一半,阿娘忽然发现了我身上半新不旧的衣裳,恍然想起什么,忙从里间翻出一身新衣——上面绣着我素喜的纹案。阿娘满含歉意地递给我新衣,轻声解释我喜欢的纹案过于繁琐,阿娘需要织的衣裳也多,这件新衣是她昨夜赶工的,便忘了早些拿给我。阿娘解释完,催着我去换新衣,新年旧衣可不好。
我心疼阿娘,看阿娘眉眼间透出些许疲惫,心里虽有话想说,仍是忍住不愿打扰阿娘暂时的歇息。毕竟,一会儿许家的旁系分支就要来主家这儿找阿娘拜年了。
我换上新衣,在旁系亲属走后进屋,想给阿娘看看她辛苦一宿的成果。阿娘却看着我恍了神,下意识地唤了声“老爷”。
我一怔,旋即沉默片刻,轻声唤了声“阿娘”。
阿娘回过神,垂下眼帘,对我挥挥手,示意我出去。我退出房间,轻轻地为阿娘掩上了门,在门外望着院中景色杵立良久。
“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知道阿娘是思念父亲了,我与父亲又生得极像,旁人一眼便能认出是亲父子。当然,父亲逝世时才一岁的我对父亲没有丝毫印象,这一切都是阿娘和大伯告诉我的。
大伯许进是爷爷的嫡长子,可惜只会随爷爷一同耕种,对读书科举是一窍不通。好在爷爷的次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许逸。自小被誉为神童,三场考试连拔头筹,为爷爷争了不少面子。爷爷为了许家重现祖上荣光,不顾长幼有序,在遗嘱中将全部家产交由父亲。而这点父亲比爷爷更肆意,父亲是完全不顾嫡庶有别。
好在大伯也认为家产在父亲手中才能更上一层楼,所以并不与父亲争抢,在老家守着地务农,赶集时才来探望我家。
只是谁也没想到,一帆风顺的父亲会遭遇如此大的打击,以至于……
我微叹一声,敛了情绪,替阿娘忙碌起了新年的各项事宜。
十六岁。
这年,我与嫡弟许梧一同参与了童试,双双中第。这个好消息传到家中,阿娘只是微微一笑。在她认知中,父亲那样优秀的人,一个小小童试,子女定然稳过。倒是大伯欢喜的很,特意提了两壶好酒几斤好肉来到我家,与我和弟弟一同喝酒吃肉,豪迈地拍着我俩的肩膀,让我俩像父亲那般,连拔头筹。
大伯与大伯母情意深厚,可大伯母却早逝。因此大伯膝下并无子女,将父亲的子女视为己出。
大伯一人将一壶半的酒喝完,醉趴在桌。我与弟弟合力将大伯抬至房中,我酒量尚可,弟弟却喝的微醺,在抬大伯的过程中,不知是醉酒还是有意,惆怅地问了句:“为什么父亲不愿陪着我们长大呢?一次科举失利而已……”
在弟弟的认知中,对父亲是有埋怨的。埋怨他为什么不肯坚持,为什么一定寻死,使原本幸福的家庭分崩离析。
我不语,将大伯抬至床上便让弟弟回房歇息了。
独自一人将大伯彻底安置好后,我转头也准备回房休息。忽然听见大伯的喃喃:
“阿逸你怎么就放弃了呢……怎么不看看栕儿等儿他们有多大出息……嗝……阿逸……”
我脚步微顿,旋即佯作未闻,走出房间,掩上了门。
父亲的一了百了,伤了多少人的心啊。
十八岁时,在母亲的催促下,我无奈与同省的樊家定亲。樊家独女,樊晚吟。我的……未婚妻?想来还是有些许无奈,素未谋面,却要相伴终生。
但我也并不很在意,毕竟这些事在安朝毫不罕见。我若不喜,大不了休妻另娶便是。当今皇帝的理念偏向男子自由,自然是给了男子足够的婚姻自主,丝毫不像先帝。
先帝是个怪人,在位时期竭力提高安朝女子地位,不知得罪多少老臣,民间也议论不休。在百姓看来,女子始终是外人,不论在娘家,婆家。
先帝在位时间不长,十七岁登基,二十三岁驾崩,在位仅六年。
可这短短六年,先帝却能将当时已有乱象的安朝稳定下来,甚至先帝提高女子地位的举措如今也尚有保留,譬如我的嫡姐许悦能学医考入尚药局,女子可与夫家和离,共同财产应平分,都是先帝在时推行的政策。
这足以见先帝的圣明,只惜,天妒。
耀明六年,先帝龙驭上宾。
因先帝无嗣,大臣推举先帝胞弟继位,也就是今上。今上继位后,为先帝上庙号,号安穆宗。同时谥号定,称安定帝。
大虑静民曰定。
十九岁。载元五十三年,皇帝驾崩。
太子继位,定先帝谥号为胡。
弥年寿考曰胡。
后改年号玄平,又称玄平元年。
先帝二皇子燕王谋反,割据一方,皇帝以雷霆手段平反,麾下车骑将军岑权一战成名。
弱冠之年,大伯为我赐字:忠安。
良辰吉日,我身穿青绿长袍,骑一匹高头大马,带着迎亲队伍前往樊家。一系列拦门及过礼后,樊家长子背新娘上轿,吹鼓手们见轿门已关新娘已到,一阵吹呼着升轿,迎新娘回了我许家府宅。众亲朋环绕身边,我与新娘跪于阿娘跟前。
“一拜天地!”
我牵她对门外天地遥拜。
“二拜祖先!”
我携她郑重叩首。
“三拜高堂!”
我望着满脸喜悦的阿娘,再度携她叩首。
“夫妻交拜!”
我凝视着她的红盖头,看不清她的脸,也不知她是何表情。
我们缓缓互拜。
随着司礼的话语,我引领着她向我的尊长,以及亲朋揖拜。
后有人牵引她在洞房静待,而我则张罗着婚宴,宴谢各方来宾,应酬不断。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天色渐暗。在亲朋的哄闹打趣声中,我入了洞房。
房外哄闹声不绝,房内她坐于床沿悄无声息。
我以喜秤挑开盖头,映入眼帘的姑娘生的面若银盘,眼如水杏,好一俏人儿。
她抬眸看我,我笑笑,伸手牵她至桌前坐下,桌上净是些红枣桂圆等物。
她倾酒,我举杯。两人无话,互相凝视着默饮合欢酒,便是完成了“合卺”。我旋即取来小剪,剪下我与她各一缕发丝,绾在一处作为我们结合的信物,此谓之“合髻”。
至于再后来?
“月明忽羞寻蔽云,鹊上柳梢鸣不听。
罗帐香软温玉怀,醉梦乡里只贪欢。”
二十三岁。
新帝登基的第一场殿试,我恰是其中应试者。
记忆中,年轻的帝王端坐殿上,缓缓扫视着众人。打量片刻,才不紧不慢地公布题目:民之于官何位。
我沉吟片刻,依先生教导,以民生展开,一针见血,洋洋洒洒写了不下千字。
后得新帝赏识,拔得头筹,钦点为状元郎,赏银百两,受封从二品,一时风光无限,成为朝堂中最年轻的从二品官员。
也是这年,家中添丁,妻子樊氏为我诞下嫡长女。
双喜临门。
二十五岁。
在阿娘的操持下,小妹许怜与袁家嫡长子袁乾成婚。袁乾对小妹甚是尊重,依着小妹的意见,迁居至浙省,让小妹不必与娘家分居两地。
小妹出嫁时是由我背上轿,她依偎在我背上,与幼年贪玩累极,赖我背上不肯下来时的姿态别无二般。
只是这次,却是少女长成,将离家了。
她在我耳旁轻轻问:“阿兄,你会不会想我?”
我笑笑:“想。要是委屈了就回来,阿兄养你一辈子。”
她又一次吐吐舌头,也笑:“才不会,袁郎对我如何,阿兄可见过的。”
我颔首,不可置否。
说来本该嫡姐许悦先出嫁,才轮得到小妹的婚事。可嫡姐醉心医学,不理亲事,若再等,只怕要将妹妹等成老姑娘了。阿娘无法,才越了嫡姐先打点小妹的亲事。只是这内里事外人不得而知,关于阿娘的“后娘做法”便又起了风言风语。
毕竟人们看热闹永远不嫌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