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书对 光与影:33号远征队 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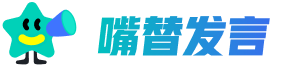 因高专业度入选
因高专业度入选

啼书

TapTap玩赏家
修改于
2025/4/29不客气地说,《光与影:33号远征队》(下称《33》)并不像许多自媒体和狂热玩家所营销的那样,是一款能够倒逼JRPG品类进步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33号》的确是为JRPG这一品类乃至于业界,注入了一股极为强劲的生命力。
如果要用极为简单的概念去阐明《33》的特点,那实际上仅用七字便足以概括,即“好钢用在刀刃上”。换而言之,主创团队Sandfall Interactive很清楚自己这个33人小团队的长短板,其对《33》这一项目的定位和规划自然也十分明了:其一,《33》是一款美术风格主导的作品;其二,Sandfall Interactive要做一款自己觉得好玩、自己喜欢的回合制游戏——说得再具体一些,这便是《33》JRPG风味的来源。
这样的项目定位和规划,使得《33》成为了一款极具特色、优劣分明的作品。当玩家操纵着主角从卢明城出发,踏入游戏中的序章时,一定会被《33》强大的视听体验所震撼:破碎的城市、颇具电影感的滤镜,以及让人心潮澎湃的配乐。
事实上,Sandfall Interactive自己也非常清楚,从卢明城出发的这一段序章游戏内容,便是《33》最吸引人或说是最适合对外展示的“牌面”。从破碎城市及其街景的视觉构建,趣味性十足的区域探索,穿插其中且密度恰到好处的情节和设定……还有游戏中最为震撼的一场演出:抹煞时刻。
在《33》中,最为核心的世界观设定便是“绘母”和“抹煞”:每过一年,名为绘母的存在便会重新绘制石纪上的倒数,而超过这个数字的个体则会被抹煞——到了《33》游戏正式开始的时间线,数字已从34被重绘为33,这也意味着所有超过了33岁的人类都会被无情地抹除。
故而在游戏开始时,男主与即将被抹煞的前女友像从前那样一起逛遍了卢明城,随后一起携手来到港口,等待着绘母重新苏醒的那刻。当绘母拿起画笔,将石板上的34改为33时,悲怆的乐曲响起,无数年轻人相拥着化作粉尘和花瓣,而男主则只能眼睁睁看着明明仍旧深爱着对方,但却因末世种种顾虑而无法继续相拥的前女友,在自己的指缝间化作花瓣和灰尘。
为了确保游戏演出的质量,《33》在人物神态的演出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当角色哭泣时,其泪痕甚至能带过脸上的灰尘。而除此之外,游戏长达八小时、多达154首的原声音乐也可谓是功不可没——想必像我一样沉溺在主界面BGM《Alicia》中,以至于一时半会不想正式开始游戏的玩家不在少数。
事实上,这种试听体验的登峰造极,其传达的是游戏极具底蕴的美学理念和核心设定表达:在游戏介绍里制作团队就已提到,游戏想要传达的,是法兰西19世纪末“美好年代”时期的风采。要想搞清楚《33》这样残酷、唯美且优雅的美学理念究竟从何而来,就得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美好年代,Sandfall Interactive又为何缅怀美好年代。
引用百度百科的介绍,美好年代/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是指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后人对此时代的回顾——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日臻成熟。
更重要的是,作为高卢雄鸡的法国,便是这一时代欧洲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尤其是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法国可谓是欧洲美好年代的先锋和缩影:其中最鲜明的例子,便是光与影的艺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正是在1895年由卢米埃尔兄弟于巴黎首次放映。这也是为什么在《33》中,绘画、音乐、舞蹈这些艺术概念会反复出现,以至于它们深深融入了游戏的核心设定、视觉奇观和敌人设计之中。
而美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象征,则是为世界带来伤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第一次成规模和制式地投入到世界规模的战争之中,人类将理性的结晶“科技”用于残杀同族,以至于酿就了“凡尔登绞肉机”这样的人间惨剧。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却被后世誉为“最伤心的赢家”:被战争消耗殆尽的外汇储备,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损失……各类经济、社会问题使得法国在一战之后便一蹶不振。换个角度来看,那些在绘母苏醒前来到港口等待抹煞的年轻人们,何尝不是在映射战争年代里,那些来到港口、等待残酷命运的年轻士兵呢?除了在离开前和爱人相拥,他们什么也做不到。
但在《33》中,仍有部分人会选择抗争这样的命运,这即是游戏的另一个重要设定,远征队。为了探明和击败抹煞的真相,仅存一年寿命的个体会组成队伍来到大陆,用自己的生命铺就道路,为后人留以希望。
在33号远征队之前的诸多远征队,可以说是游戏中核心的叙事构成,其中包括了游戏的远征队文档收集。更巧妙的是,这种碎片化叙事深度结合了场景叙事,玩家在获得了文档之后,需要结合场景内的诸多信息,才能窥探当年远征队遭遇的意外和他们做出的努力。其中攀岩远征队的设定尤为让人动容,因为玩家能通过攀岩来到不同场景,正是靠这支远征队此前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尸体和付出成为了33号远征队得以成功的基石。
而之所以如此夸赞游戏的重要演出和碎片叙事,实际上也暴露了《33》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游戏主体部分的故事和叙事大多都极为糟糕,甚至毫不留情地说,《33》的诸多剧作硬伤完全是埋没了不俗的核心设定和背后美学理念。在开头卢明城优秀的探索之后,游戏长达十个小时的第一章基本没有什么有效信息可言,彻底损毁了游戏的叙事节奏和玩家期望,这种满天飞的废话和谜语人倒也符合许多人对于JRPG的刻板印象——由于剧透的可能性,这里便不宜过度延展。
而同样饱受争议且存在巨大缺陷的部分则是游戏的玩法和数值设计。在玩家社群,你会经常观察到十分奇妙的现象:许多玩家会直言不讳地吐槽《33》往回合制里塞这样频繁的QTE简直是反人类,或是嘲讽自己有生之年绝对想象不到自己会在JRPG中应付快慢刀——但与此同时,这名玩家大概率会一边怒骂一边继续体验《33》。
这便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33》对类魂与回合制的大胆创新和结合,不一定是多么优秀合理的游戏设计,但却的确是无比新奇和具有生命力的游戏体验和框架——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众对于JRPG乃至于回合制的刻板认知和体验惯性,带来了足够眼前一亮的设计。
如果要谈论《33》的玩法体验,那就无法绕开即便是轻度玩家耳熟能详的两个系列:《黑暗之魂》和《女神异闻录》。甚至说得更难听一点,除了前文所提到的试听体验和美学理念,《33》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缝合怪:你能在《33》里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以坐火(篝火)和BOSS挑战划分游戏探索节点的流程框架;你能在《33》里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体力药、装备(属性特长)、等级加点的成长循环;你能在《33》里体验到《女神异闻录5》那充满既视感的队友好感度、瞄准设计和钩锁移动……甚至能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不死人会随着受伤和死亡而改变外貌(外型充满血渍和灰尘)的微小细节设定。
但这套回合制+类魂的玩法框架设计确实是在解决传统回合制的一部分缺陷痛点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体验缺陷和问题——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它们都是“新”的存在,这也造就了《33》极为奇妙的游戏体验:在一章中前期,玩家往往要顶着一刀就被敌人劈死的压力去适应这种穿插在回合制之间的QTE,打破原本低专注度、低操作性的回合制体验。在这一阶段,玩家的体验近似于刻板印象里的类魂,备受秒杀体验煎熬的同时通过反复死亡这样残酷的教训去熟悉诸如快慢刀之类的动作模组和机制。当玩家克服了这一阻碍,通过QTE打出了漂亮的完美闪避和弹反时,其反馈感是极高的。
而在一章后期和二章前期,《33》的局外BD(养成构筑)、局内的回合制策略和QTE操作渐渐达成了某种体验上的平衡,玩家也开始适应游戏的机制和手感,甚至能轻松触及游戏的伤害上限(9999),其玩法体验开始走高走稳。
进入二章中后期,游戏却又陷入了新的困局:游戏体验逐渐变得无趣和不合理了起来——而这种体验上的变化,和游戏的数值及系统设计息息相关。在《33》中,除了前文提及的类魂成长循环,游戏的养成和构筑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符纹和灵光系统,也即游戏的Perk系统(被动或是配件)。实际上这类系统在游戏设计中无比常见,例如《空洞骑士》中的护符系统,就是通过解锁新的护符和护符槽位提升角色数值或是解锁角色机制,同时让玩家根据不同的需求(探图、清怪、BOSS等)探索和搭配不同护符组合。但《33》的Perk系统,和《空洞骑士》并不全然相同,反而更像是《神之天平》——《33》和《神之天平》的相似之处,在于采用了Cost(费用)这一机制,给予了玩家更多构筑上的选择权。
不同于易于设计者把控bd强度的槽位设计,《33》和《神之天平》采用的Cost机制和两部作品给出的极大Cost上限拓宽了组合的可能性与上限。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制作团队Sandfall Interactive不仅没有足够的数值设计底力,也丝毫不在机制上设限:增伤机制全部叠算,角色增伤机制50%保底,最高可达到200%,某些角色一章就可以拿到前置条件极为简单的再动技能,甚至存在一回合两动这样的无脑符纹配件。
可以料想,当玩家体验到二章中后期时,其丰富的Perk库、大量的Cost点数和一定的游戏理解已经足够其摸索出让游戏数值框架崩塌的套路了。如果一旦放任玩家秒天秒地秒一切,那估计玩家制作组精心设计的敌人动作模组都看不到。为了应对这一难题,《33》极为不明智地加入了一个非常呆板且糟糕的设计,9999的伤害数值上限。加之《33》虽采用了相似的Perk设计,但其所谓BD体验就是不断累加更强的符纹,根本没有《空洞骑士》或是《神之天平》那样根据需求切换和尝试不同BD的新奇体验。所以玩家在二章中后期的体验十分单调乏味:因为游戏的单次伤害上限是9999,所以玩家大部分时候要做的,不过是围绕着一个能够使用多段高伤技能的主C配队,随后不断重复清怪即可。BOSS和小怪的区别,不过是撑过你一发还是两发罢了——没有操作性,没有BD趣味性,也没有策略性。
但一旦熬过二章中后期这一艰难时期,玩家就可以解开9999的数值上限,体验到彻底的数值爽游。之前的枷锁被彻底打破,玩家可以尽情实验不同BD的伤害上限,轻轻松松打出许多JRPG和类魂作品这辈子都见不到的超大数字,通过不同套路和机制花式碾压敌人。
用ARPG类比一下,就是《33》让玩家从前期受苦为主的类魂体验到中期的平衡操作和BD的类暗黑,再体验到后期横扫千军的类无双——这样带有泄洪快感的流程和框架设计,不说放在JRPG和回合制品类里,即便放在整个游戏市场,也确实是足够新奇。
这样以来,便不难窥清Sandfall Interactive为何能通过处女作就拿下MC媒体均分和Steam玩家好评率90+了:那就是通过风格化的试听和美学优势先发制人,而后通过足够新奇的体验弥补游戏设计层面的硬伤——并非完美,但的确足够巧妙,且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如果要用极为简单的概念去阐明《33》的特点,那实际上仅用七字便足以概括,即“好钢用在刀刃上”。换而言之,主创团队Sandfall Interactive很清楚自己这个33人小团队的长短板,其对《33》这一项目的定位和规划自然也十分明了:其一,《33》是一款美术风格主导的作品;其二,Sandfall Interactive要做一款自己觉得好玩、自己喜欢的回合制游戏——说得再具体一些,这便是《33》JRPG风味的来源。
这样的项目定位和规划,使得《33》成为了一款极具特色、优劣分明的作品。当玩家操纵着主角从卢明城出发,踏入游戏中的序章时,一定会被《33》强大的视听体验所震撼:破碎的城市、颇具电影感的滤镜,以及让人心潮澎湃的配乐。
事实上,Sandfall Interactive自己也非常清楚,从卢明城出发的这一段序章游戏内容,便是《33》最吸引人或说是最适合对外展示的“牌面”。从破碎城市及其街景的视觉构建,趣味性十足的区域探索,穿插其中且密度恰到好处的情节和设定……还有游戏中最为震撼的一场演出:抹煞时刻。
在《33》中,最为核心的世界观设定便是“绘母”和“抹煞”:每过一年,名为绘母的存在便会重新绘制石纪上的倒数,而超过这个数字的个体则会被抹煞——到了《33》游戏正式开始的时间线,数字已从34被重绘为33,这也意味着所有超过了33岁的人类都会被无情地抹除。
故而在游戏开始时,男主与即将被抹煞的前女友像从前那样一起逛遍了卢明城,随后一起携手来到港口,等待着绘母重新苏醒的那刻。当绘母拿起画笔,将石板上的34改为33时,悲怆的乐曲响起,无数年轻人相拥着化作粉尘和花瓣,而男主则只能眼睁睁看着明明仍旧深爱着对方,但却因末世种种顾虑而无法继续相拥的前女友,在自己的指缝间化作花瓣和灰尘。
为了确保游戏演出的质量,《33》在人物神态的演出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当角色哭泣时,其泪痕甚至能带过脸上的灰尘。而除此之外,游戏长达八小时、多达154首的原声音乐也可谓是功不可没——想必像我一样沉溺在主界面BGM《Alicia》中,以至于一时半会不想正式开始游戏的玩家不在少数。
事实上,这种试听体验的登峰造极,其传达的是游戏极具底蕴的美学理念和核心设定表达:在游戏介绍里制作团队就已提到,游戏想要传达的,是法兰西19世纪末“美好年代”时期的风采。要想搞清楚《33》这样残酷、唯美且优雅的美学理念究竟从何而来,就得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美好年代,Sandfall Interactive又为何缅怀美好年代。
引用百度百科的介绍,美好年代/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是指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后人对此时代的回顾——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日臻成熟。
更重要的是,作为高卢雄鸡的法国,便是这一时代欧洲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尤其是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法国可谓是欧洲美好年代的先锋和缩影:其中最鲜明的例子,便是光与影的艺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正是在1895年由卢米埃尔兄弟于巴黎首次放映。这也是为什么在《33》中,绘画、音乐、舞蹈这些艺术概念会反复出现,以至于它们深深融入了游戏的核心设定、视觉奇观和敌人设计之中。
而美好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象征,则是为世界带来伤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第一次成规模和制式地投入到世界规模的战争之中,人类将理性的结晶“科技”用于残杀同族,以至于酿就了“凡尔登绞肉机”这样的人间惨剧。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却被后世誉为“最伤心的赢家”:被战争消耗殆尽的外汇储备,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损失……各类经济、社会问题使得法国在一战之后便一蹶不振。换个角度来看,那些在绘母苏醒前来到港口等待抹煞的年轻人们,何尝不是在映射战争年代里,那些来到港口、等待残酷命运的年轻士兵呢?除了在离开前和爱人相拥,他们什么也做不到。
但在《33》中,仍有部分人会选择抗争这样的命运,这即是游戏的另一个重要设定,远征队。为了探明和击败抹煞的真相,仅存一年寿命的个体会组成队伍来到大陆,用自己的生命铺就道路,为后人留以希望。
在33号远征队之前的诸多远征队,可以说是游戏中核心的叙事构成,其中包括了游戏的远征队文档收集。更巧妙的是,这种碎片化叙事深度结合了场景叙事,玩家在获得了文档之后,需要结合场景内的诸多信息,才能窥探当年远征队遭遇的意外和他们做出的努力。其中攀岩远征队的设定尤为让人动容,因为玩家能通过攀岩来到不同场景,正是靠这支远征队此前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尸体和付出成为了33号远征队得以成功的基石。
而之所以如此夸赞游戏的重要演出和碎片叙事,实际上也暴露了《33》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游戏主体部分的故事和叙事大多都极为糟糕,甚至毫不留情地说,《33》的诸多剧作硬伤完全是埋没了不俗的核心设定和背后美学理念。在开头卢明城优秀的探索之后,游戏长达十个小时的第一章基本没有什么有效信息可言,彻底损毁了游戏的叙事节奏和玩家期望,这种满天飞的废话和谜语人倒也符合许多人对于JRPG的刻板印象——由于剧透的可能性,这里便不宜过度延展。
而同样饱受争议且存在巨大缺陷的部分则是游戏的玩法和数值设计。在玩家社群,你会经常观察到十分奇妙的现象:许多玩家会直言不讳地吐槽《33》往回合制里塞这样频繁的QTE简直是反人类,或是嘲讽自己有生之年绝对想象不到自己会在JRPG中应付快慢刀——但与此同时,这名玩家大概率会一边怒骂一边继续体验《33》。
这便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33》对类魂与回合制的大胆创新和结合,不一定是多么优秀合理的游戏设计,但却的确是无比新奇和具有生命力的游戏体验和框架——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众对于JRPG乃至于回合制的刻板认知和体验惯性,带来了足够眼前一亮的设计。
如果要谈论《33》的玩法体验,那就无法绕开即便是轻度玩家耳熟能详的两个系列:《黑暗之魂》和《女神异闻录》。甚至说得更难听一点,除了前文所提到的试听体验和美学理念,《33》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缝合怪:你能在《33》里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以坐火(篝火)和BOSS挑战划分游戏探索节点的流程框架;你能在《33》里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体力药、装备(属性特长)、等级加点的成长循环;你能在《33》里体验到《女神异闻录5》那充满既视感的队友好感度、瞄准设计和钩锁移动……甚至能体验到《黑暗之魂》中不死人会随着受伤和死亡而改变外貌(外型充满血渍和灰尘)的微小细节设定。
但这套回合制+类魂的玩法框架设计确实是在解决传统回合制的一部分缺陷痛点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体验缺陷和问题——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它们都是“新”的存在,这也造就了《33》极为奇妙的游戏体验:在一章中前期,玩家往往要顶着一刀就被敌人劈死的压力去适应这种穿插在回合制之间的QTE,打破原本低专注度、低操作性的回合制体验。在这一阶段,玩家的体验近似于刻板印象里的类魂,备受秒杀体验煎熬的同时通过反复死亡这样残酷的教训去熟悉诸如快慢刀之类的动作模组和机制。当玩家克服了这一阻碍,通过QTE打出了漂亮的完美闪避和弹反时,其反馈感是极高的。
而在一章后期和二章前期,《33》的局外BD(养成构筑)、局内的回合制策略和QTE操作渐渐达成了某种体验上的平衡,玩家也开始适应游戏的机制和手感,甚至能轻松触及游戏的伤害上限(9999),其玩法体验开始走高走稳。
进入二章中后期,游戏却又陷入了新的困局:游戏体验逐渐变得无趣和不合理了起来——而这种体验上的变化,和游戏的数值及系统设计息息相关。在《33》中,除了前文提及的类魂成长循环,游戏的养成和构筑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符纹和灵光系统,也即游戏的Perk系统(被动或是配件)。实际上这类系统在游戏设计中无比常见,例如《空洞骑士》中的护符系统,就是通过解锁新的护符和护符槽位提升角色数值或是解锁角色机制,同时让玩家根据不同的需求(探图、清怪、BOSS等)探索和搭配不同护符组合。但《33》的Perk系统,和《空洞骑士》并不全然相同,反而更像是《神之天平》——《33》和《神之天平》的相似之处,在于采用了Cost(费用)这一机制,给予了玩家更多构筑上的选择权。
不同于易于设计者把控bd强度的槽位设计,《33》和《神之天平》采用的Cost机制和两部作品给出的极大Cost上限拓宽了组合的可能性与上限。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但制作团队Sandfall Interactive不仅没有足够的数值设计底力,也丝毫不在机制上设限:增伤机制全部叠算,角色增伤机制50%保底,最高可达到200%,某些角色一章就可以拿到前置条件极为简单的再动技能,甚至存在一回合两动这样的无脑符纹配件。
可以料想,当玩家体验到二章中后期时,其丰富的Perk库、大量的Cost点数和一定的游戏理解已经足够其摸索出让游戏数值框架崩塌的套路了。如果一旦放任玩家秒天秒地秒一切,那估计玩家制作组精心设计的敌人动作模组都看不到。为了应对这一难题,《33》极为不明智地加入了一个非常呆板且糟糕的设计,9999的伤害数值上限。加之《33》虽采用了相似的Perk设计,但其所谓BD体验就是不断累加更强的符纹,根本没有《空洞骑士》或是《神之天平》那样根据需求切换和尝试不同BD的新奇体验。所以玩家在二章中后期的体验十分单调乏味:因为游戏的单次伤害上限是9999,所以玩家大部分时候要做的,不过是围绕着一个能够使用多段高伤技能的主C配队,随后不断重复清怪即可。BOSS和小怪的区别,不过是撑过你一发还是两发罢了——没有操作性,没有BD趣味性,也没有策略性。
但一旦熬过二章中后期这一艰难时期,玩家就可以解开9999的数值上限,体验到彻底的数值爽游。之前的枷锁被彻底打破,玩家可以尽情实验不同BD的伤害上限,轻轻松松打出许多JRPG和类魂作品这辈子都见不到的超大数字,通过不同套路和机制花式碾压敌人。
用ARPG类比一下,就是《33》让玩家从前期受苦为主的类魂体验到中期的平衡操作和BD的类暗黑,再体验到后期横扫千军的类无双——这样带有泄洪快感的流程和框架设计,不说放在JRPG和回合制品类里,即便放在整个游戏市场,也确实是足够新奇。
这样以来,便不难窥清Sandfall Interactive为何能通过处女作就拿下MC媒体均分和Steam玩家好评率90+了:那就是通过风格化的试听和美学优势先发制人,而后通过足够新奇的体验弥补游戏设计层面的硬伤——并非完美,但的确足够巧妙,且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