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批评对 银与绯 的评价
《银与绯》,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对味儿的传统日式RPG原创IP手游了。
上手就是子安武人标志性的变态念白,对吧,“子安又配吸血鬼了”,给你拉回了遥远的过去。
注意,这里说的是日式/日系游戏,不是“二次元游戏”,前者说的可能是《勇者斗恶龙》系列,可能是《传说》系列,可能是《轨迹》系列,有一个形象丰富的角色群像,呈现以游戏为载体的舞台剧演出,认真要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后者,则可能是以《舰队collection》、《刀剑乱舞》或《少女前线》肇始,它的故事是没有尽头的,周期性更新面向特定审美偏好的新角色,取悦特定的受众。
卖老婆。
所以今天如果某些游戏媒体会把《银与绯》描述为一种“格调特别不同的二次元游戏”,实际上可能说的是这种日式舞台剧表现的RPG游戏在手游领域已经消亡多时了,划不出一个独立的分类。
今天你去看日区Appstore游戏畅销榜TOP100,半壁江山都是各种热门动漫IP改编产品,七大罪、海贼王、王者天下、SD高达,原创IP内容的RPG产品,恰恰只有我们国产的米哈游三件套与《鸣潮》,象征着手游时代日本同业创作能力的全面败北。
在2015前后的几年,这曾经是世嘉与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等传统日本游戏大厂的舒适区,某某战记,某某传说,某某骑士团,某某境界线,好似有一套通行的命名规则,就像你今年看到的许多国产卫星,异环,虚环,火环,归环。
二次元拟人“老婆GAME”在中国爆发量产前的一两年,你会看到上海曾经的几家游戏小龙都在尝试做自己的日式RPG手游,一种统一的包装形式是宣传我们家的游戏请到了多少大牌日本CV献声。那个时代标志性的行业笑话,谁家新游你要是没请到钉宫理惠配音,漕河泾出门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银与绯》,在通稿挂出来的子安武人、三木真一郎与能登麻美子之外,其实也是请到了钉宫理惠配音的,配的是一个序章就出场的跟班小男孩。
钉宫,配小男孩?
???
基本上从一个日式RPG游戏的声优阵容和配音文本量,就能够看出它的成本规模和公司的重视程度,没什么钱的小公司,只会配少数重点段落,附加大量咿咿呀呀的语气表达。
所以像是《银与绯》这样主线与活动剧情90%全程配音,我们一般就叫作“经费爆炸”,体现出制作方沐瞳与幕后字节的壕气,今天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家日本公司还会做这个规格的RPG手游。
就是立足与面向日本市场,试图去复活一个消亡的品类,重新激活玩家需求。
然后《银与绯》首发当天呢,游戏批评在订阅列表看到两个文章标题:
游戏葡萄:沐瞳偷偷做的第一款二游,今天红了;
游戏大观:第一次做全球同步发行、死磕不太主流2D演出,这款二游今天赌赢了!
观感就是:
开局爆香槟,你这个游戏是要遭呀?(四川口音)
没两天《银与绯》在Taptap的评分就从“万众期待,战绩可查”被玩家干到了5.5。
红了,火了,爆了,炸了,赢了,感觉你们这些中国游戏人整天就不是在北上广深成杭做游戏,而是在德黑兰做游戏。
豪华日本声优阵容,在2015年,是向后来被市场定义为“二次元”的中国ACG爱好者推销新游的核心卖点,也是今天你想要让一款中国出海网游立足日本的刚需。
而在2025年,今天会自称为“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成长于一个“国漫崛起”的时代,阅片经历在日本动画之外有了更多的国产选择,它从小接触的手机网游可能更多是自带山新与皇贞季团队们国语配音的国风游戏,它的青少年记忆里没有多少子安武人与能登麻美子的成分,那你精心策划的“听觉盛宴”,难免就会变成“叽里呱啦一点听不懂,让人无名火起”。
这里体现的就是十年间中国两个世代年轻“二次元”的需求画像流变。
反映出的是许多中国“出海游戏企业”普遍的认知误区,你把产品销售到任何一个海外国家都要注重“本地化”改造,但是把一个立足日本文化的全球同步产品放在自己的家乡销售,它好像理所应当就觉得不需要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怎么卖给日本人也可以怎么卖给中国人,像2015年一样默认日语配音。
它可能会有一种幻觉,哪个二次元日漫ACG爱好者打开我这个游戏听到了子安武人的配音,还会想要切换到中文语音包,是否多此一举,有什么大病。
本地化失误,至少应该在子安武人这个开场白前后给中国玩家弹窗提示,提供一个主动切换到国语配音的机会。
《银与绯》的核心养成玩法与付费框架,不用细看你都知道是硬套了《胜利女神NIKKE》,选型本身很糟糕,NIKKE的真实卖点完全就不在玩法与付费。
《银与绯》的发行时间点,恰好又选在了腾讯发行NIKKE国服的一个月后,无可避免会被作为高频比较对象,然后腾讯团队给NIKKE国服做了一系列新手20连自选、福利加码与场景切换提速等体验优化。
《银与绯》的许多抽卡付费设计,照搬的都是日本市场的惯例,像是开局必出随机SSR的新手卡池必须付费购买98+128元礼包抽取,这在NIKKE本体,或是B站代理的日本产品《公主连结》与《赛马娘》,都有常见的类似设定。
而在中国玩家,习惯的是30抽或50抽左右的新手卡池,游戏研发商会给你在邮箱里塞上一堆抽卡券,注册首日稍微肝一肝,第一张SSR角色就免费送你了,最好还要提供SSR自选。
所以这么多中国玩家不满《银与绯》的付费强度,不满高频弹出的付费礼包,不一定是它没玩过NIKKE,没玩过《剑与远征》,没有接触过所有日本原产手机网游,而是不满你上来就把中国玩家当成日本人来整,大量的差评都是情绪性反应。
无视中国年轻玩家今天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特殊性。
比较聪明的做法,其实是把《银与绯》这样一个明显日本市场定制的产品首先放在日韩发行,半年或一年后,逐步扩散到港台与东南亚,再进入国内,届时针对性根据不同地区用户的消费习惯调整付费项目与礼包销售策略,逐步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付费项目,作为优惠。
中国玩家不一定是嫌弃你把游戏内容卖多贵,而是嫌弃你没有特殊优待自己人。
但是字节嘛,你懂的,就是喜欢玩一些高难度的杂技,搞个赌赢了的大新闻,全球同步发行,那么在付费项目调优上就很难有操作空间,容易造成不同地区玩家的比较不满。
联系到《银与绯》上线之前几乎没看到什么媒体投放铺垫,全球同步发行大概率是来自哪个新来的大老板仓促的拍脑袋需求。
林林总总还有许多细节上的UI设计失误,导致产品的视觉易用性很差,即使开局强制教程跑了快半小时,多数玩家仍然不太好理解布阵操作与不同职业角色的差异。
当然,抛开上述非常行业视角的评价,游戏批评实际上非常认可与欣赏《银与绯》在美术、音乐与剧本等软实力内容的创作,西木康智的配乐,MILET演唱的主题曲,那太对味儿了,作为一个日系RPG手游,《银与绯》提供的“番剧体验”甚至远好于世嘉与SE十年前的大部分骑士团与传说创作。
而你看到的许多差评,都会针对《银与绯》的剧情演出,各种看不懂,各种转折生硬,各种高中生文学。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今天中国市场尚存最成功的几款日系RPG,米哈游三件套,有哪一个不是日常在社区被玩家车剧情车角色设定车得死去活来?
这一代自称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是被番茄小说、快看漫画,乃至于是被海棠文学喂大的,从小通过B站UP主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解说来了解一部番剧一部电影,你对它们的阅读审美能有多高的期待?
一面是要求所有的剧情演出都要提供跳过,一面是嫌弃所有的游戏编剧写得不好,“不如我自己上”。
个别在研团队,声称要启用星云奖获奖作者来搞二游剧本与世界观创作,顺应NGA与贴吧的呼声,给每一个演出模块都标注文案责任人。
在游戏批评看来,你就是把雨果奖、布克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者搬过来,最终混乱的风评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你就写自己热爱与擅长的,爱跳不跳,爱玩不玩。
这一代自称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是如此普遍的,肤浅,以至于所有跟二次元沾点边的游戏,底下富集的都是两种对立型态的评论:
你这个游戏里的女性角色是不是穿太少了,太媚男,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宅女玩家,不需要我们氪金了;
你这个游戏里的女性角色露得不够多,服务意识不够强,还卖小男孩,是不是团队被小仙女脑控了,滚粗二次元。
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复杂叙事,普遍缺爱与普遍的认同得失焦虑。
为什么你的游戏不是专门为我服务的,为什么你不能更爱我一点?
今天你在中国处理“游戏本地化”、“如何讨好年轻人”,研究的其实就是怎么承担一整个世代的教育失败,社交网络与短视频深度泛滥于童年的后果。
是不是感觉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更加深重了?
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在游戏在文化内容消费里寻求的是一系列被关注,被优待与被追捧的优越感,所有的内容包装都是表象。最值得被解决的问题,不是产能,不是UE5,不是工业化,而是陪伴感,游戏能不能持续提示玩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游戏能不能让玩家的每一笔消费都想象“我又赚到了”。
下一代“赌赢了”的二游,最需要的关注的不再是如何写好一个故事,如何让玩家在三个月后还能记住一个角色,记住一场战斗,而是如何让游戏成为玩家的伴侣,如何让游戏成为玩家的妈妈。
是不是有点儿明白远遁新加坡开发AI女友的蔡浩宇为什么又领先你几个版本了?
上手就是子安武人标志性的变态念白,对吧,“子安又配吸血鬼了”,给你拉回了遥远的过去。
注意,这里说的是日式/日系游戏,不是“二次元游戏”,前者说的可能是《勇者斗恶龙》系列,可能是《传说》系列,可能是《轨迹》系列,有一个形象丰富的角色群像,呈现以游戏为载体的舞台剧演出,认真要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后者,则可能是以《舰队collection》、《刀剑乱舞》或《少女前线》肇始,它的故事是没有尽头的,周期性更新面向特定审美偏好的新角色,取悦特定的受众。
卖老婆。
所以今天如果某些游戏媒体会把《银与绯》描述为一种“格调特别不同的二次元游戏”,实际上可能说的是这种日式舞台剧表现的RPG游戏在手游领域已经消亡多时了,划不出一个独立的分类。
今天你去看日区Appstore游戏畅销榜TOP100,半壁江山都是各种热门动漫IP改编产品,七大罪、海贼王、王者天下、SD高达,原创IP内容的RPG产品,恰恰只有我们国产的米哈游三件套与《鸣潮》,象征着手游时代日本同业创作能力的全面败北。
在2015前后的几年,这曾经是世嘉与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等传统日本游戏大厂的舒适区,某某战记,某某传说,某某骑士团,某某境界线,好似有一套通行的命名规则,就像你今年看到的许多国产卫星,异环,虚环,火环,归环。
二次元拟人“老婆GAME”在中国爆发量产前的一两年,你会看到上海曾经的几家游戏小龙都在尝试做自己的日式RPG手游,一种统一的包装形式是宣传我们家的游戏请到了多少大牌日本CV献声。那个时代标志性的行业笑话,谁家新游你要是没请到钉宫理惠配音,漕河泾出门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银与绯》,在通稿挂出来的子安武人、三木真一郎与能登麻美子之外,其实也是请到了钉宫理惠配音的,配的是一个序章就出场的跟班小男孩。
钉宫,配小男孩?
???
基本上从一个日式RPG游戏的声优阵容和配音文本量,就能够看出它的成本规模和公司的重视程度,没什么钱的小公司,只会配少数重点段落,附加大量咿咿呀呀的语气表达。
所以像是《银与绯》这样主线与活动剧情90%全程配音,我们一般就叫作“经费爆炸”,体现出制作方沐瞳与幕后字节的壕气,今天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家日本公司还会做这个规格的RPG手游。
就是立足与面向日本市场,试图去复活一个消亡的品类,重新激活玩家需求。
然后《银与绯》首发当天呢,游戏批评在订阅列表看到两个文章标题:
游戏葡萄:沐瞳偷偷做的第一款二游,今天红了;
游戏大观:第一次做全球同步发行、死磕不太主流2D演出,这款二游今天赌赢了!
观感就是:
开局爆香槟,你这个游戏是要遭呀?(四川口音)
没两天《银与绯》在Taptap的评分就从“万众期待,战绩可查”被玩家干到了5.5。
红了,火了,爆了,炸了,赢了,感觉你们这些中国游戏人整天就不是在北上广深成杭做游戏,而是在德黑兰做游戏。
豪华日本声优阵容,在2015年,是向后来被市场定义为“二次元”的中国ACG爱好者推销新游的核心卖点,也是今天你想要让一款中国出海网游立足日本的刚需。
而在2025年,今天会自称为“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成长于一个“国漫崛起”的时代,阅片经历在日本动画之外有了更多的国产选择,它从小接触的手机网游可能更多是自带山新与皇贞季团队们国语配音的国风游戏,它的青少年记忆里没有多少子安武人与能登麻美子的成分,那你精心策划的“听觉盛宴”,难免就会变成“叽里呱啦一点听不懂,让人无名火起”。
这里体现的就是十年间中国两个世代年轻“二次元”的需求画像流变。
反映出的是许多中国“出海游戏企业”普遍的认知误区,你把产品销售到任何一个海外国家都要注重“本地化”改造,但是把一个立足日本文化的全球同步产品放在自己的家乡销售,它好像理所应当就觉得不需要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怎么卖给日本人也可以怎么卖给中国人,像2015年一样默认日语配音。
它可能会有一种幻觉,哪个二次元日漫ACG爱好者打开我这个游戏听到了子安武人的配音,还会想要切换到中文语音包,是否多此一举,有什么大病。
本地化失误,至少应该在子安武人这个开场白前后给中国玩家弹窗提示,提供一个主动切换到国语配音的机会。
《银与绯》的核心养成玩法与付费框架,不用细看你都知道是硬套了《胜利女神NIKKE》,选型本身很糟糕,NIKKE的真实卖点完全就不在玩法与付费。
《银与绯》的发行时间点,恰好又选在了腾讯发行NIKKE国服的一个月后,无可避免会被作为高频比较对象,然后腾讯团队给NIKKE国服做了一系列新手20连自选、福利加码与场景切换提速等体验优化。
《银与绯》的许多抽卡付费设计,照搬的都是日本市场的惯例,像是开局必出随机SSR的新手卡池必须付费购买98+128元礼包抽取,这在NIKKE本体,或是B站代理的日本产品《公主连结》与《赛马娘》,都有常见的类似设定。
而在中国玩家,习惯的是30抽或50抽左右的新手卡池,游戏研发商会给你在邮箱里塞上一堆抽卡券,注册首日稍微肝一肝,第一张SSR角色就免费送你了,最好还要提供SSR自选。
所以这么多中国玩家不满《银与绯》的付费强度,不满高频弹出的付费礼包,不一定是它没玩过NIKKE,没玩过《剑与远征》,没有接触过所有日本原产手机网游,而是不满你上来就把中国玩家当成日本人来整,大量的差评都是情绪性反应。
无视中国年轻玩家今天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特殊性。
比较聪明的做法,其实是把《银与绯》这样一个明显日本市场定制的产品首先放在日韩发行,半年或一年后,逐步扩散到港台与东南亚,再进入国内,届时针对性根据不同地区用户的消费习惯调整付费项目与礼包销售策略,逐步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付费项目,作为优惠。
中国玩家不一定是嫌弃你把游戏内容卖多贵,而是嫌弃你没有特殊优待自己人。
但是字节嘛,你懂的,就是喜欢玩一些高难度的杂技,搞个赌赢了的大新闻,全球同步发行,那么在付费项目调优上就很难有操作空间,容易造成不同地区玩家的比较不满。
联系到《银与绯》上线之前几乎没看到什么媒体投放铺垫,全球同步发行大概率是来自哪个新来的大老板仓促的拍脑袋需求。
林林总总还有许多细节上的UI设计失误,导致产品的视觉易用性很差,即使开局强制教程跑了快半小时,多数玩家仍然不太好理解布阵操作与不同职业角色的差异。
当然,抛开上述非常行业视角的评价,游戏批评实际上非常认可与欣赏《银与绯》在美术、音乐与剧本等软实力内容的创作,西木康智的配乐,MILET演唱的主题曲,那太对味儿了,作为一个日系RPG手游,《银与绯》提供的“番剧体验”甚至远好于世嘉与SE十年前的大部分骑士团与传说创作。
而你看到的许多差评,都会针对《银与绯》的剧情演出,各种看不懂,各种转折生硬,各种高中生文学。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今天中国市场尚存最成功的几款日系RPG,米哈游三件套,有哪一个不是日常在社区被玩家车剧情车角色设定车得死去活来?
这一代自称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是被番茄小说、快看漫画,乃至于是被海棠文学喂大的,从小通过B站UP主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解说来了解一部番剧一部电影,你对它们的阅读审美能有多高的期待?
一面是要求所有的剧情演出都要提供跳过,一面是嫌弃所有的游戏编剧写得不好,“不如我自己上”。
个别在研团队,声称要启用星云奖获奖作者来搞二游剧本与世界观创作,顺应NGA与贴吧的呼声,给每一个演出模块都标注文案责任人。
在游戏批评看来,你就是把雨果奖、布克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者搬过来,最终混乱的风评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你就写自己热爱与擅长的,爱跳不跳,爱玩不玩。
这一代自称二次元的中国年轻人,是如此普遍的,肤浅,以至于所有跟二次元沾点边的游戏,底下富集的都是两种对立型态的评论:
你这个游戏里的女性角色是不是穿太少了,太媚男,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宅女玩家,不需要我们氪金了;
你这个游戏里的女性角色露得不够多,服务意识不够强,还卖小男孩,是不是团队被小仙女脑控了,滚粗二次元。
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复杂叙事,普遍缺爱与普遍的认同得失焦虑。
为什么你的游戏不是专门为我服务的,为什么你不能更爱我一点?
今天你在中国处理“游戏本地化”、“如何讨好年轻人”,研究的其实就是怎么承担一整个世代的教育失败,社交网络与短视频深度泛滥于童年的后果。
是不是感觉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更加深重了?
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在游戏在文化内容消费里寻求的是一系列被关注,被优待与被追捧的优越感,所有的内容包装都是表象。最值得被解决的问题,不是产能,不是UE5,不是工业化,而是陪伴感,游戏能不能持续提示玩家“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游戏能不能让玩家的每一笔消费都想象“我又赚到了”。
下一代“赌赢了”的二游,最需要的关注的不再是如何写好一个故事,如何让玩家在三个月后还能记住一个角色,记住一场战斗,而是如何让游戏成为玩家的伴侣,如何让游戏成为玩家的妈妈。
是不是有点儿明白远遁新加坡开发AI女友的蔡浩宇为什么又领先你几个版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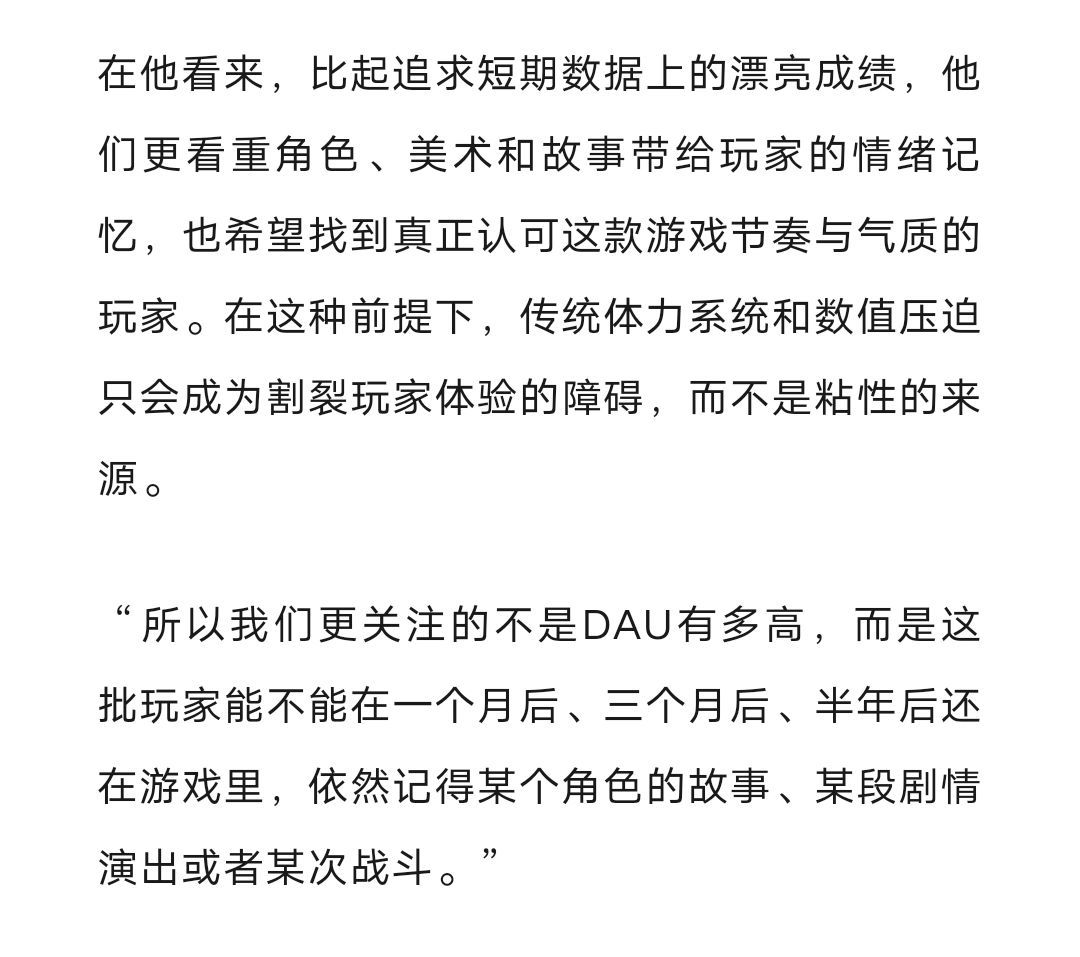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