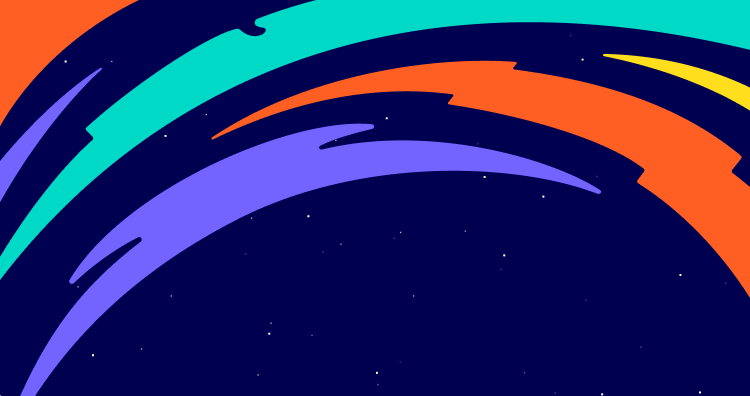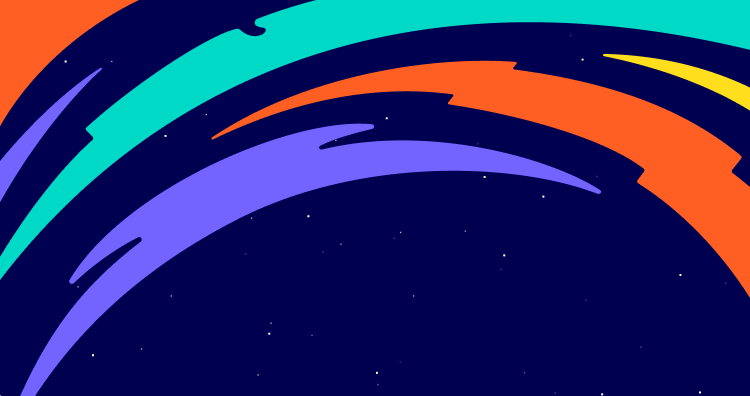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汤显祖《牡丹亭》
从前便是个偏爱国风的人,看见惊梦这画风就不知暗地里欢喜了好几回,一张一张的认真截图,好似柳梦梅与杜丽娘梦里私会,一如年少的窃喜。风是轻的,柳是绿的,就是连梦里的少女,情绪里都染上了晚霞的粉橙色。我们沉浸于故事,欢喜在画风,感羡于爱情。
可我分明记得,他们的故事,是“游园惊梦”,是“惊梦”,纵使你千般万般执手相依,道什么“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忽而梦醒,魂牵梦萦的容颜不见,枕边冷汗涔涔,华榻罗裙,惊了这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梦。
又似梦似真。
游戏里是以柳生的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他说他走过竹园幽径,绕过画屏,也解过迷阵。他用水墨给这世界染上颜色,她便驻足观望,痴痴守候。
游戏中,终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他们最后相遇在牡丹亭,以蝶为寄。
然后呢?当我们想着是否应从此执手,生死不离时。画面定格,游戏说,它没有然后。或许,只不过是梦中二人不愿醒罢了。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